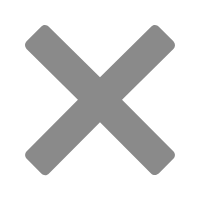-
美人皮
第二章
爹听到我的尖叫。
他冲过来,抓起娘的手指含在口中。
娘呜咽了一声,那动静就像李婆子家刚生的小奶猫。
爹抱起娘回了房。
留我自己守着一箱子皮影和红嫁衣。
我娘手巧,我们姐妹的嫁衣全由她自己缝制。
我摸着那些刺绣,突然看到左前襟有块不显眼的污渍。
心口没来由地一紧。
我又抓起右边的袖口。
果然,也有块污渍。
登时,我如堕冰窟!
……
大姐嫁人那年,我八岁。
我哭着不让她走,她便给我口中塞了块糖。
我含着糖在她怀里哭睡了,等醒过来时,嫁衣左前襟都是我流出来的口水。
口水里带着糖,怎么也擦不掉。
后来二姐出嫁,我又哭。
二姐哄着我,给我涂上跟她一样的红口脂玩。
结果我一个不小心将口脂蹭到了她的袖口上。
……
手心被金丝扎得生疼。
这件火红的嫁衣裳,是大姐的也是二姐的。
那么,她们究竟嫁了没有?
大姐和二姐,到底去哪儿了?
晚饭又是爹做的。
他忿忿地扔了竹笋,给我做了一盘青豆焖豆腐。
娘一直在房里躺着,饭也没吃。
吃过饭,爹洗碗,撵我回屋去试衣裳。
今儿天黑得极快。
我才洗了脸,就听见爹娘房里传来响声。
爹娘恩爱,常常青天白日的,房里就发出叫声。
我早就习以为常。
可今夜不同。
我听见那声音里,还夹着几声旁的动静。
细细听来,竟然是大姐二姐在叫我的名字!
壮着胆子,我推开房门。
声音是从西厢发出来的。
夜里寒凉,那声音叫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却还是硬着头皮钻进门去。
西厢空荡荡的,只有一箱皮影。
声音正是从箱子里发出来的。
平常这箱子我爹娘都上锁,许是今日我娘受了伤,我爹心里只惦记着她,匆忙之间竟忘锁了。
“娴姐儿,娴姐儿……”
声音细细的,却越来越清晰。
我手脚冰凉,猛地鼓起劲儿,一把掀开了那个檀木箱子!
箱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皮影。
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冷风吹破了半面窗户纸,一张皮影晃了晃。
我低头拣了出来。
这张我认得。
那年,爹说皮影里那张九彩石裂开了。
后来大姐出嫁,没多久,这箱子里就多了张新的九彩石。
我又埋头找出一张八卦镜。
这是二姐出嫁后,补进来的新皮影。
这两张皮又细又嫩,据说是我娘亲手画的画染的色。
因为年头短,不像旁个那样干干巴巴,还带着一丝弹性。
平常我娘宝贝得紧,每次晾晒都要自己来,从不让我去碰。
我将皮影举起来,借着月光细细打量。
突然,大姐二姐的声音一齐响了起来。
“娴姐儿快逃,娘要剥你的皮呢!”
我吓得手一松腿一软。
皮子掉在地上,我也跌坐在地。
惊恐让我透不过气来。
脑子都浑了。
我不明白,大姐二姐的声音为什么会从皮子里发出来。
姐姐让我逃,我又能逃到哪里去?
这些年,虽说乡下民风开放,可我娘守着旧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连带着我都没把这个破落的庄子给逛完过。
我也才十三岁,被娘养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逃到哪儿去?
我的心快从嗓子眼蹦了出来。
“姐姐……”我哆哆嗦嗦地问。
“娘为什么要剥我的皮?你们也是被娘剥了皮吗?”
那两张皮子突然不出声了。
西厢寂静得可怕。
后背的寒毛突然竖了起来。
我猛地回头。
一张惨白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月光下,我娘蹲在我身后,手指缠着药布,渗出的血却还是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娴姐儿啊,你在干什么……”
娘的声音阴戚戚地响起,拉着丝儿一样,余音绕梁。
我眼前一黑。
直接吓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