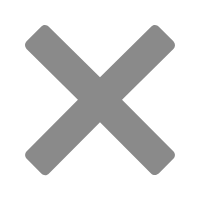-
女儿香
第4章
“你这女儿体格特殊,不能用平常的法子倒吊,得正着吊。”
爹按照张瘸子说的,浸泡了黑狗血的绳子,穿过我胳膊下面在脖颈交汇,借助我的头发固定在房梁上。
我能清楚听到头发与头皮分离的声音,迸裂声扎根在脑子里,我的精神高度紧张。
爹用的小刀是我托村口刀匠磨了又磨,非常锋利。
划在脚踝凸起的骨头上只能感觉都一丝的疼痛,随后是冰凉,身体好似有什么跑了出去。
因为被吊起的头发连带着眼皮,我只能努力将眼睛向下看,透过自己的脚尖勉强看清楚一点。
是血,是我的血。
血流很快,滴答滴答一碗就满了。
可爹还不满足,手中的利刃重复了之前的操作划开了另一只脚。滴答滴答又满了另一只碗。
“爹,我渴。”
爹兴高采烈捧着两只血碗出去,绑在我头顶的绳子松了松,脚尖堪堪能挨到地面,又因为脚踝的疼痛而落不到地。
放脚脚疼,不放,头皮疼。
上上下下传来的疼痛让我的神经紧张起来,院子里爹磨木头的声音时时刻刻拉扯着这跟紧绷的弦。
“这香种真不错啊,出了两碗血还是这么精神。”
我求救的哀嚎声被爹认为是精神的象征。
视线模糊实际,我仿佛看到了大姐二姐。
她们的脸从高处渐渐降落,那黑紫的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随着贴近皮肤凹陷下去。
“三妹,你要做香种吗?”
“三妹,跟我们走吧,跟我们走吧。”
三妹,三妹,三妹......
为什么要叫我,为什么都来叫我。
我张了张嘴想要喊出声,却没什么作用,只能看着两双倒挂的手贴上我的脖子,窒息感随之而来,我仿佛体会到了大姐二姐死之前的绝望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
许是我的挣扎见了效,大姐二姐骤然离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存在。
幽幽的香甜从院子里传出来,香味弥漫整个院子。
这意味着,线香做成了。
而我的身前,站着我的傻娘。
她捏着一块骨头对我嘿嘿嘿笑道,“吃,吃肉。”
而猪圈里的猪正分成两堆不知道在啃食着什么,只能从拥挤的缝隙中看到一只肿胀的手搭在那里。
而那手上,带着二姐曾经编的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