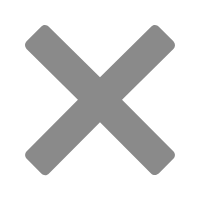-
村民哄抢我船上的海货后,全村傻眼了
第1章
五年前,我父亲开渔船满载而归,经过黑石湾时,船底被暗桩刺破。
船沉了,父亲溺亡,而那一船新鲜海产被附近村民打捞一空。
后来才知道,那些暗桩是村民故意布下的,他们专等渔船触礁,好抢走渔获。
母亲想讨回公道,可村民团结一致,毁灭证据,威胁证人,最终只能作罢。
母亲气病交加,不到一年就郁郁而终。
五年后,我开着渔船,同样在黑石湾“触礁”。
看着蜂拥而来抢夺海产的村民,我趴在船板上虚弱地喊:“别拿,那些海货不能吃!”
他们嗤之以鼻,争抢着说这海蜇真肥,凉拌最鲜美。
但他们不知道,我养的是澳洲灯水母……
晨雾像扯碎的棉絮漂浮在海面。
我正弯腰检查活水舱的供氧泵,一个沙哑带笑的声音从岸上飘来。
“小伙子,这船货色可以啊!”
我抬头,看见个穿着褪色防水服的老渔民蹲在缆桩上。
古铜色的脸上皱纹深刻,像被海风雕琢过的礁石。
他眯眼打量着我满舱的海货,手腕上那道蜈蚣似的疤痕格外扎眼。
和父亲当年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喉头滚动,面上却挤出个憨厚的笑。
“嗐,也还行吧,今早上刚捞的,打算去市场上碰碰运气。”
我继续摆弄着氧气管,声音放得平缓。
九年前就是这个男人,用假潮汐灯把我父亲的船引向暗礁区。
父亲船沉那夜,他带着村民在礁石边“捡”了整整三船货。
老渔民利落地跳上我的船艉板,防水靴踩出湿漉漉的脚印。
“去市场卖多亏啊!”
他热络地拍我肩膀,
“今早龙王礁那边全是黄鱼群!银晃晃的跟铺了层金箔似的!”
他眼睛瞟着我舱里肥美的螃蟹,
“你要信我老王,现在跟我抄近路过去,我给你高价。”
我搓着手露出为难相:
“龙王礁?我爹常说那边暗礁凶险……”
话说一半故意咽回去,低头看向地板。
老王脸色微不可察地一僵,随即笑得更深,露出被烟熏黄的牙:
“老皇历啦!现在那儿早清了航道。”
说话间,他已经稳当当坐在船头,掏出皱巴巴的烟盒。
眯眼望着前方若隐若现的礁群轮廓。
他时不时回头冲我咧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
“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跑船几年了?”
他状似随意地问,眼睛却像钩子似的刮过我船舱里那些肥美的海货。
“才跑两年多。”
我憨厚地挠挠头,手下稳稳把着舵轮,
“跟我爹学了点皮毛,自己瞎折腾。”
“嘿!两年就能捞到这么旺的货?后生可畏啊!”
他吐着烟圈,声音带着夸张的赞叹,
“你爹是哪条船上的?没准我还认识哩!”
我的心猛地一揪,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爹……早就不跑船了。现在就在家歇着。”
手指无意识地收紧,舵轮冰冷的触感刺着掌心。
王老五“哦”了一声,眼珠转了转,没再追问。
他指着左前方一片看似平静的水域:
“往那儿偏点,避开下面那片暗礁群——瞧见没?
水色深的那块!底下全是尖石头,去年老陈家的船就在那儿栽了跟头!”
我顺从地转动舵轮,心里冷笑:
去年老陈的船,不就是被你们引到那儿凿沉的?
“叔您可真神!”
我故意露出钦佩的表情,“这海况您都门清!”
“哈哈!四十年饭不是白吃的!”
他得意地拍着胸脯,防水服发出哗啦的响声,
“我跟你讲,这龙王礁看着凶,其实藏着宝!
只要找对路子——”
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
“渔业公司在那儿设了临时收购点,现捞现结,价钱是这个数!”
他又比出五根手指。
我配合地瞪大眼睛:
“五成?这么高?”
“骗你干啥!”
他凑近来,带着鱼腥和烟味的热气喷在我脸上,
“公司老板是我表亲!专收好货送高档酒楼!
你这些货色,他们绝对抢着要!”
他越说越兴奋,手指比划着:
“待会儿到了地方,你啥也不用管!
我喊人来过秤,现钱直接塞你手里!
比你去市场跟那帮二道贩子磨嘴皮子强多了!”
我心里翻涌着恶心,脸上却挤出犹豫:
“可是……我爹总说便宜莫贪……”
“哎哟!我的傻小子!”
老王急得直拍大腿,
“你爹那老思想过时啦!现在讲究的是渠道!关系!”
他眼珠一转,忽然压低声音,
“这么着——叔看你投缘,今天这船货,叔再给你多争取半成价!
就当给侄子的见面礼!”
他说着就要掏手机:
“我这就给收购点打电话,让他们备好现金等咱们!”
我赶忙拦住他,脸上挤出感激又不安的笑:
“叔!这……这怎么好意思……”
我低头咬着烟没接话。
他以为我是腼腆,其实我是怕眼里的冰碴子戳穿他。
九年前父亲沉船后,就是这个王老五,一边捞着父亲船里漂出的鱼箱,一边对哭晕的母亲嚷“女人家别碍事”。
渔船突突驶向雾霭深处。
老王坐在船头得意地哼起渔歌,盘算着待会儿怎么发信号让村民拦船。
他不知道的是,我拉的是澳洲灯水母。
而龙王礁的村民,最爱把“捡来”的海鲜直接扔进大锅炖煮。
老王此刻还在美滋滋地吐着烟圈,仿佛已经闻到今晚全村鱼汤的鲜香。
“有啥不好意思!”
他一把推开我的手,嗓门洪亮,
“咱们渔民就得互相帮衬!
你爹要是知道你有这机遇,肯定乐得合不拢嘴!”
他边说边飞快地按着手机键盘,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冷笑。
又回头对我露出一个过分热情的笑容:
“看!穿过这片海,就能看到俺们村子了!
小伙子,你今天可要走大运了!”